■ 张翠萍
我前几天收到高塘镇的老战友宏利给儿子娶亲的消息,便在一个清晨自驾从西安出发,沿着连霍高速一路向东行驶约70公里又拐上榆蓝高速段,不久便进入高塘镇。
前往宏利家需要穿过高塘镇主街道,我摇下车窗深深吸了一口塬上的新鲜空气,只见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,塬上的风裹着泥土的腥甜,卷过青砖灰瓦的老街。此时恰逢高塘镇集市,虽还是清晨,主街道已开始熙熙攘攘起来。沿街道两旁簇拥着卖衣卖布的、卖针卖线的、卖葱卖蒜的小商小贩。旭日暖阳穿透云霞洒满大地,秦岭山脉中的这座悠久乡镇笼罩在一片福瑞霞光中。此时高塘镇的集市,像一锅慢炖的浆水汤,在晨光里咕嘟咕嘟地沸腾起来。
印象最深的是十字街口用遮阳伞撑起的麻花铺子,油锅前总是三人在操作,一个老者揉面,两妇人将面团在案板上反复揉搓成绳状,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准确坠入滚烫油锅,锅内瞬间腾起一股白烟。买麻花的人排成长队,一位裹头巾的老太太絮叨着:“老味道,每个集市都会来买,孙子最爱吃。”接过油纸包着的麻花,咬一口脆响,碎渣扑簌簌落在衣襟上,让食客唇齿留香。
转过街角,饸饹床子正压着荞麦面饸络。摊主先在饸饹床子装上和好的荞麦面,屁股一拧便坐在木杠子上,向下一用力,只听“吱呀”一声,饸饹落入翻滚的沸水,捞起时泛着黄亮亮的光,调上辣子油,顿时勾起了食欲。
隔壁凉粉摊的铜勺敲着瓷碗,“辣子调美醋调酸,来上一碗解心宽”,摊主言语间舀一勺莹白的凉粉,浇上芥末蒜汁,冲鼻上头的一碗凉粉便大功告成。
透着金黄色的糍粑摊有几位食客正在大快朵颐,山里人常用土豆作为原料制作糍粑,配以西红柿、白萝卜、绿辣椒、葱段、蒜泥、香油等煸炒后制成的汤汁臊子,金黄色泽、香气四溢、甘甜微辣爽口的陕西关中糍粑让人垂涎欲滴、回味无穷,成为高塘镇风味独特的待客佳肴。
豆腐脑承载着儿时的记忆和生活的烟火气,只见担子前围满了人,木桶揭开时腾起热气,用铜勺旋起洁白如玉的豆腐脑于碗中,淋上料汁和咸菜碎,只见几位银发老人捧着青花瓷碗抵着碗沿啜饮,衫子蹭上酱色也不顾。有人蹲在石阶上吸溜着浆水面,酸汤里泡着腌萝卜,让我想起爷爷常挂在嘴边的念叨“消暑的浆水暖胃的面”。
菜市口堆着新刨的毛芋,还沾着顾田村的红泥。最热闹的地方是花馍铺子,龙凤呈祥的馍饼上点着胭脂红,系着围裙的馍铺主家笑吟吟道:“来几个带回去,这可是咱老陕独创的非遗。”
返程时,我不禁回望这暮色中的塬上小镇,街道铺就的青石板路若隐若现,屋檐下的石凳上,几个老汉就着如血残阳,翻着那本毛边的《话说高塘塬》。山坡间牧羊人吆喝羊儿的乡音悠扬回荡,风掠过松柏,仿佛把百年前的呐喊也揉进了如今的集市,远处炊烟正从千家万户的灶膛升起直插云霄,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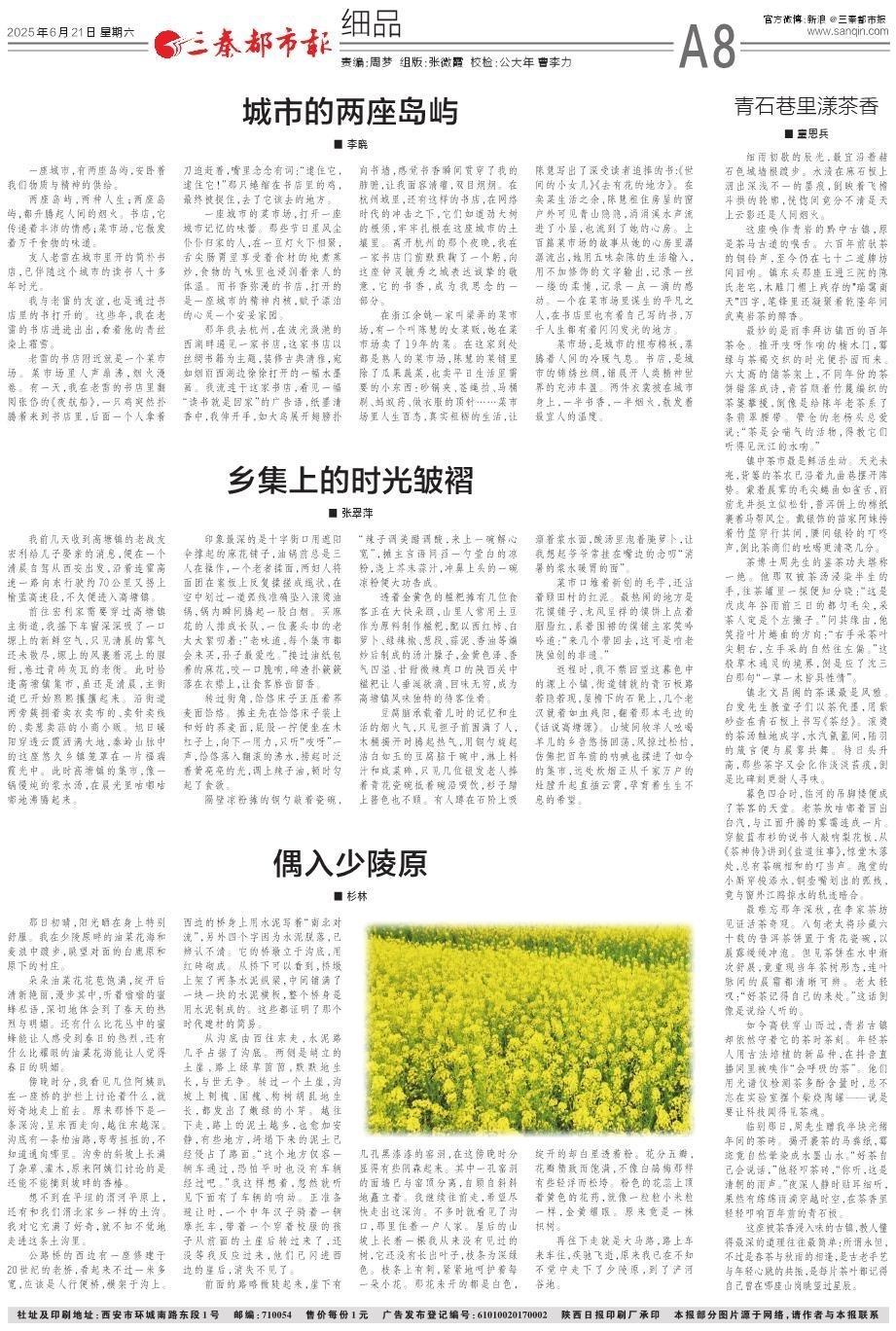
 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964号
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964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