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高晓文
华阴市西南的旷野上,罗敷镇古城村一截黄褐色夯土墙斜倚着暮色。指尖抚过厚厚的夯层,能触到嵌在土里的卵石——这是三千年前周人特意掺进去的,为的是让土墙更结实,也像给这段历史嵌了枚沉甸甸的印章——这便是告平城遗址。如今这里国道、高速公路纵横而过,高压电塔在遗址旁屹立,现代电流的嗡鸣和千年前的誓言,竟在风里轻轻碰撞。
公元前1046年的清晨,周武王的战车碾过潼关的霜。四百辆战车列成阵,三千虎贲士的甲胄映着朝阳,四万五千甲士的戈矛尖上,挑着还没散尽的夜雾。他们向东走,走了整整三天,烟尘漫过黄河故道,终于在牧野停了脚。对面纣王的军队漫山遍野,可细看便知,那些穿着破烂甲衣的,多是被抓来的奴隶,还有满脸菜色的百姓。当周军的战鼓响起,他们忽然扔下兵器,转身就往朝歌方向跑——他们盼着周人来,盼着能有口饱饭吃。
当周军的马蹄踏到华阴罗敷河谷口,武王忽然勒住马。他抬头,正看见西岳华山——既像一把直插云天的剑,又像一尊稳稳当当的鼎。商王朝的烽烟,仿佛还在眼前飘;身边诸侯的甲胄,还在“叮叮当当”响着。他忽然想起渭水河畔的姜子牙,那个直钩钓鱼的老头,曾对他说:“治国如钓鱼,急不得,要等民心归。”
武王下令:“停军,筑台。”士兵们放下戈矛,拿起锄头,挖起当地的黄土,掺上河里的卵石,一层层夯。夯土的号子声里,土台慢慢长高。清《华阴县志》里写:“敷水南山石山之敷谷有告平城。相传武王伐纣告太平于此。”后来考古的人来,发现夯土里的卵石竟排成星斗的形状,和周原出土的甲骨文“告”字对得上——原来周人筑台时,早把“以天道告太平”的心思,藏进了黄土里。
话音落时,风正好吹过华山,带着松涛的声儿,像天地在应和。诸侯们跟着举杯,士兵们把戈矛往地上顿了顿,“哐当”一声,震得土台上的黄土都簌簌落下。那一天,这方土台有了名字——告平城。
当地老农说,每到春分,太阳斜照时,告平城残垣的影子,会和罗敷河的水纹拼成个太极图。这话听着像传说,可1988年文物普查时,真测出来遗址的范围:东西约45米,南北380米,残墙高2到4米,夯土里的鹅卵石,确实是周代的。站在残垣下,能看见不远处的工业园区,发电厂的凉水塔热气腾腾,石材加工厂哒哒哒的敲击声,和千年前战马奔驰的蹄声,竟有几分相似。
夕阳西下时,残垣的影子拉得很长,像一条通往过去的路。风里有渭水的潮气,有农田的麦香,还有千年前武王的誓言。那些嵌在夯土里的卵石,像一颗颗星星,沉默地看着这片土地——看着农人春种秋收,看着孩子在田埂上跑,看着现代的汽车从遗址旁开过。
告平城的残垣,虽只剩半截土墙,却把“太平”两个字,种进了华夏的土里,长了千年,还在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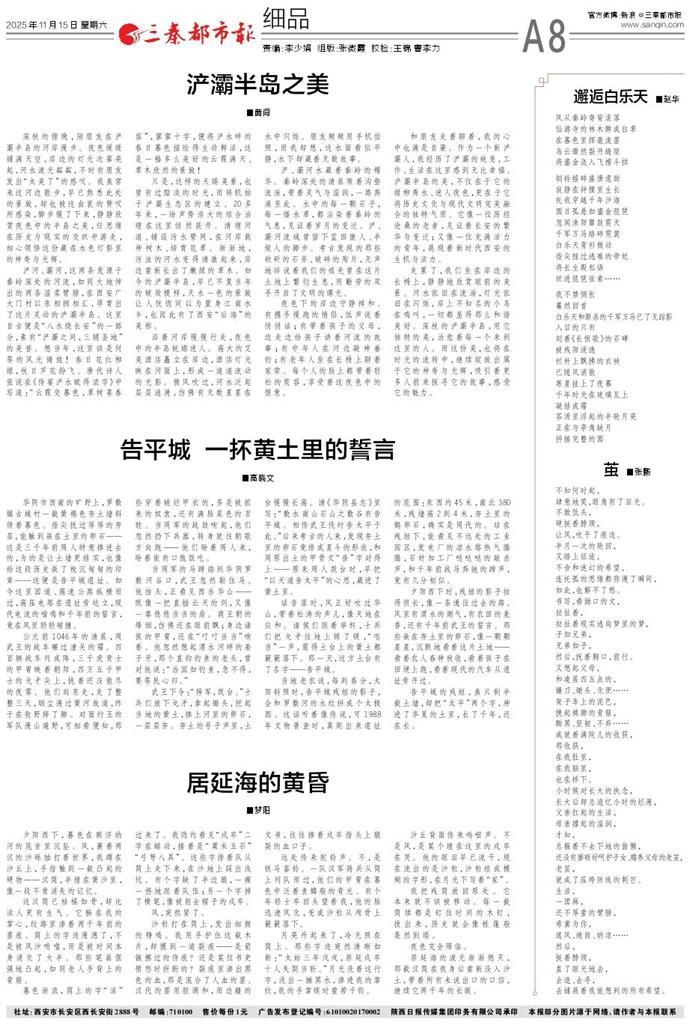
 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964号
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964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