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宋华梅
老屋在成为老屋之前,还是一间刚刚建好的新屋。
老屋的墙体是用优质的黄泥捣碎,用剁碎的稻草和清水搅拌在一起,壮汉们用脚踩跺,直到将泥巴踩到黏稠为止,再将其放入制成的模子里面,形成一块块成型的土砖。
老屋与我同岁,诞生于1988年,母亲常说我是在新房出生的。
父亲家中兄弟四个,用母亲的话来说,就是穷得叮当响。分家以后,父母亲咬着牙起了这间房,只有一间的拱房。土坯砖摞起来,房顶上铺着草席,盖一层薄瓦。但父母亲开心得很。他们尚且年轻,二女儿刚刚出生,好在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。整个拱房内只有一个房间,其他地方都算作大厅,用来摆放庄稼和农具。蒲城人将厨房叫做灶火,一个简单的石棉瓦搭造的小小灶火在拱房的外面,依着房间而建。
千禧年,我十二岁,父母亲决定再起一间房。这次的房子大一些,拱房建得很高,旁边还有两间单边溜,这话听着颇为术语,就是在拱房的外面左侧,再起两间平房,一间作为我和姐姐的卧室,一间作为杂物室。那是我刚刚小学毕业准备升入初中的暑假,母亲要为整个工程队的人做饭,一日三餐,忙忙碌碌根本无法停歇。具体要为多少人做饭,做了多久,因为年代久远我已经忘记,也无从考证。母亲去世以后,很多的数据均无法考证,若是问父亲,大抵也是以不清楚忘记了来回答。新建房屋的时候,并没有盖灶火,所以母亲依旧在那个石棉瓦房搭建的屋子里烹饪饭菜。
有一间属于自己的、干净卫生的厨房,是母亲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。
老屋如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,偶有风雨交加的夜晚,它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,宛若老人夜里沉睡之后的呓语。
时间一晃,到了2020年。舅舅准备在老家修建房子。父亲和母亲合计了一下,也决定盖个厨房和卫生间。这一年我和姐姐的孩子都大了一些,父母亲尚且健康,母亲终于拥有了她梦寐以求的大灶火,灶台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泥瓦匠搭建的,干净卫生,填上一点点柴火就烧得很旺,父亲正愁柴禾没处使用。村子里的老人们不再喜欢大锅大灶,纷纷使用煤气灶。父母亲长期居住西安,只有夏日时才回老家避避暑,所以并未购置煤气灶。也正是如此,才使得我可以继续吃到大锅大灶柴火饭,看到袅袅炊烟。
或许这场景以后只能存在于文学作品中,而不能展现在孩子的眼前,时代在发展,袅袅炊烟在我的家乡都难得一见了。
母亲的厨房非常宽敞且明亮,她一直引以为傲。听姐姐说,母亲不止一次告诉姐姐,厨房可比你西安的厨房大很多,干净又卫生,那一年母亲61岁。
厨房和卫生间建好之后,我和姐姐带着孩子们回了趟老家。十月时节,阴雨绵绵,几日后稍微放晴。坐在屋檐下看云,连带着飒飒作响的树叶,都弥漫着自由的味道。我搬了一方小桌,和父母姐姐、两个孩子在院子里喝茶闲聊。时间仿佛凝滞,就如同这院里的清风,屋顶的白云,还有门口的老树,和二十年前相比别无二致,而这匆匆逝去的二十年,也不过是夏日午后的一场绮梦罢了。
老屋老了,但是经过父母亲的修葺,老屋又焕发了新的神采。母亲也老了。去年6月,母亲突发疾病,倒在了她心心念念的厨房。本以为经过治疗总能留下母亲的命,但彩云易散世事难料。
老屋,不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间屋子,而是一个认识许久的故人,是呼啸而过的悠悠岁月,是见证了母亲一生的长者,是我心头抹不掉的故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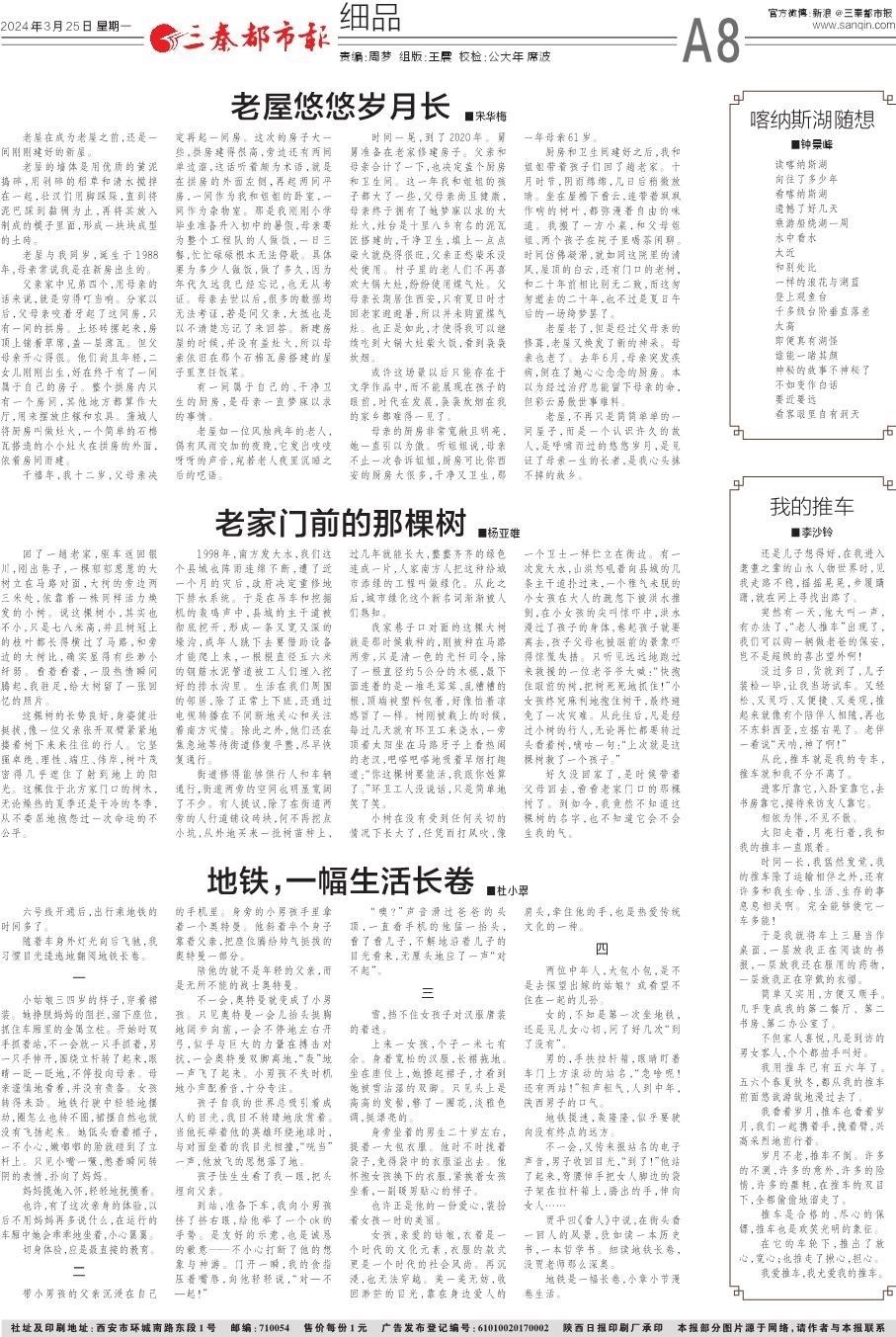
 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964号
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964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