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杜小翠
六号线开通后,出行乘地铁的时间多了。
随着车身外灯光向后飞驰,我习惯目光逶迤地翻阅地铁长卷。
一
小姑娘三四岁的样子,穿着裙装。她挣脱妈妈的阻拦,溜下座位,抓住车厢里的金属立柱。开始时双手抓着站,不一会就一只手抓着,另一只手伸开,围绕立杆转了起来,眼睛一眨一眨地,不停投向母亲。母亲谨慎地看着,并没有责备。女孩转得来劲。地铁行驶中轻轻地摆动,圈怎么也转不圆,裙摆自然也就没有飞扬起来。她低头看着裙子,一不小心,嫩嘟嘟的脸就碰到了立杆上。只见小嘴一噘,憋着瞬间转阴的表情,扑向了妈妈。
妈妈揽她入怀,轻轻地抚摸着。
也许,有了这次亲身的体验,以后不用妈妈再多说什么,在运行的车厢中她会乖乖地坐着,小心翼翼。
切身体验,应是最直接的教育。
二
带小男孩的父亲沉浸在自己的手机里。身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个奥特曼。他斜着半个身子靠着父亲,把座位腾给帅气挺拔的奥特曼一部分。
陪他的就不是年轻的父亲,而是无所不能的战士奥特曼。
不一会,奥特曼就变成了小男孩。只见奥特曼一会儿抬头挺胸地阔步向前,一会不停地左右开弓,似乎与巨大的力量在搏击对抗,一会奥特曼双脚离地,“轰”地一声飞了起来。小男孩不失时机地小声配着音,十分专注。
孩子自我的世界总吸引着成人的目光,我目不转睛地欣赏着。当他托举着他的英雄环绕地球时,与对面坐着的我目光相撞,“咣当”一声,他放飞的思想落了地。
孩子怯生生看了我一眼,把头埋向父亲。
到站,准备下车,我向小男孩挤了挤右眼,给他举了一个ok的手势。是友好的示意,也是诚恳的歉意——不小心打断了他的想象与神游。门开一瞬,我的食指压着嘴唇,向他轻轻说,“对—不—起!”
“噢?”声音滑过爸爸的头顶,一直看手机的他猛一抬头,看了看儿子,不解地沿着儿子的目光看来,无厘头地应了一声“对不起”。
三
雪,挡不住女孩子对汉服唐装的着迷。
上来一女孩,个子一米七有余。身着宽松的汉服,长裙拖地。坐在座位上,她撩起裙子,才看到她被雪沾湿的双脚。只见头上是高高的发髻,簪了一圈花,淡雅色调,挺漂亮的。
身旁坐着的男生二十岁左右,提着一大包衣服。他时不时拢着袋子,免得袋中的衣服溢出去。他怀抱女孩换下的衣服,紧挨着女孩坐着,一副暖男贴心的样子。
也许正是他的一份爱心,装扮着女孩一时的美丽。
女孩,亲爱的姑娘,衣着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元素,衣服的款式更是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。再沉浸,也无法穿越。美一美无妨,收回渺茫的目光,靠在身边爱人的肩头,牵住他的手,也是热爱传统文化的一种。
四
两位中年人,大包小包,是不是去探望出嫁的姑娘?或看望不住在一起的儿孙。
女的,不知是第一次坐地铁,还是见儿女心切,问了好几次“到了没有”。
男的,手扶拉杆箱,眼睛盯着车门上方滚动的站名,“急啥呢!还有两站!”粗声粗气,人到中年,陕西男子的口气。
地铁提速,轰隆隆,似乎要驶向没有终点的远方。
不一会,又传来报站名的电子声音,男子收回目光,“到了!”他站了起来,弯腰伸手把女人脚边的袋子架在拉杆箱上,腾出的手,伸向女人……
贾平凹《看人》中说,在街头看一回人的风景,犹如读一本历史书,一本哲学书。细读地铁长卷,没贾老师那么深奥。
地铁是一幅长卷,小章小节漫卷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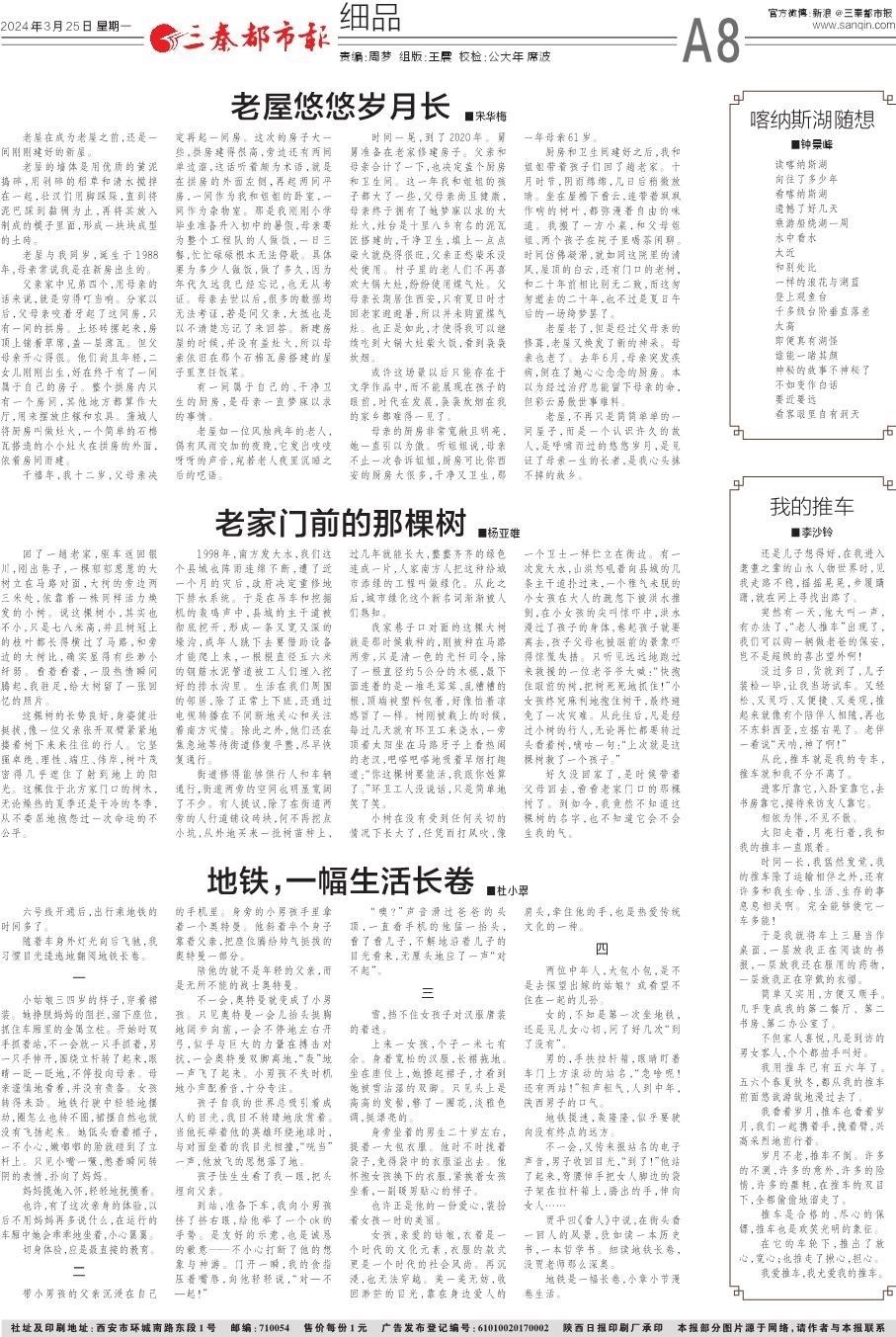
 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964号
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964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