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程晓平
一个周末,小区门口卖水果的小摊贩在地上摆了一堆塑料盒子装的水晶柿子,红艳艳的色彩中夹杂了些许的粉白,散发出不可抗拒的诱惑。可爱的小模样瞬间就刺激了我的视觉和味觉。还说啥呢,十元一盒不搞价,拿下再说。
打开包装先尝一个,熟悉的甜味瞬间就弥漫了整个口腔。心理学上说甜味食物能够让人产生愉悦心理,这小小的柿子也让人的好心情油然而生。
在房前屋后的众多树木中,和人距离最近、感情最铁的肯定是柿子树。它不挑地域,无论山沟坡地还是荒滩旱原,只要栽下去,几乎不用管护,几年就能挂果,据说能寿逾百年。柿子也叫柿果,它比野生的黑枣大出许多,但没有黑枣核多、涩味的缺憾,柿子自然成熟或者经过加工后甘甜可人,吃一口,满嘴果香。
霜降一过,满树的叶子经不起寒霜的洗礼,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秋风扫荡得所剩无几,只有那些吃霜变红的叶子还在顽强地守候,陪伴着柿子共度余生。这时的柿子颜色由黄变红,呈现鲜亮的诱人色彩,味道逐渐褪去生涩,潇洒地挂在枝头,仰头望去,就像一个个红红的小灯笼,在深秋的冷风里摇曳生姿。
记得小时候,八月过后在灞河南岸的山沟里割草,那时柿子还只有核桃大。小伙伴们兵分两路,一路把生涩的柿子摘下来,悄悄地塞到温暖的水稻田里做好记号,只要一天时间再挖出来就可以食用,温热中夹杂些许生涩,美其名曰“暖柿子”。其他伙伴上树把柿子连树枝一起折下,架到树梢最高处以浓密的枝叶遮挡,绝对不能让麻野雀或者眼尖的人发现,否则就白忙活一场,几天后就会自然软透成熟,吃起来略有甜味还算软糯,这叫“架柿子”。孩子们这些带着野性的食用方法和母亲的巧手比起来,似乎还不在一个层面。母亲把快成熟了的生柿子放到一个瓦瓮里,中间放一个拳头大的梨子,密封一周后再打开,柿子在梨子的熏陶下就变得色泽红艳、软糯香甜、美味无比,这叫“烘柿子”。
吃过太多的柿子,有一段时间,我一见柿子就心生厌烦,暗自发誓一辈子都不想再吃这样粗鄙的水果。尽管柿子很多,但母亲从不浪费一个。她把柿子去皮晒成柿子疙瘩,就连柿子皮也要收集起来,“吃”过霜后的柿皮能“长”出“白霜”,存放到容器里是哄娃的美食。入冬前,父母两人还把挑拣出来的完整柿子送上房顶,一个挨一个放到用苞谷秸秆铺成的温床上,上面再严严实实覆盖一层苞谷秸秆防止鸟儿啄食。大雪纷飞的时节,贵客临门,母亲以水温柿招待亲戚,孩子们也能跟着沾光吃上一口鲜味。
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飞快地流转,如今的我已经进入中年。久在都市,世上最美丽的风景却在回乡下老家的路上,那里有自然与人文混合装点的美丽画卷;尝遍美食,世上最甜蜜的口感可能就是柿子,那种滋味陪伴我度过的一段成长时光,苦涩而甜蜜。柿子,我发誓下辈子都不想再吃的食物,至今却牢牢地在我味觉内存里占据着一席之地。柿子的复合滋味,一定是随着生命的密码深藏在灵魂深处,任凭岁月更迭,才下舌尖,又上心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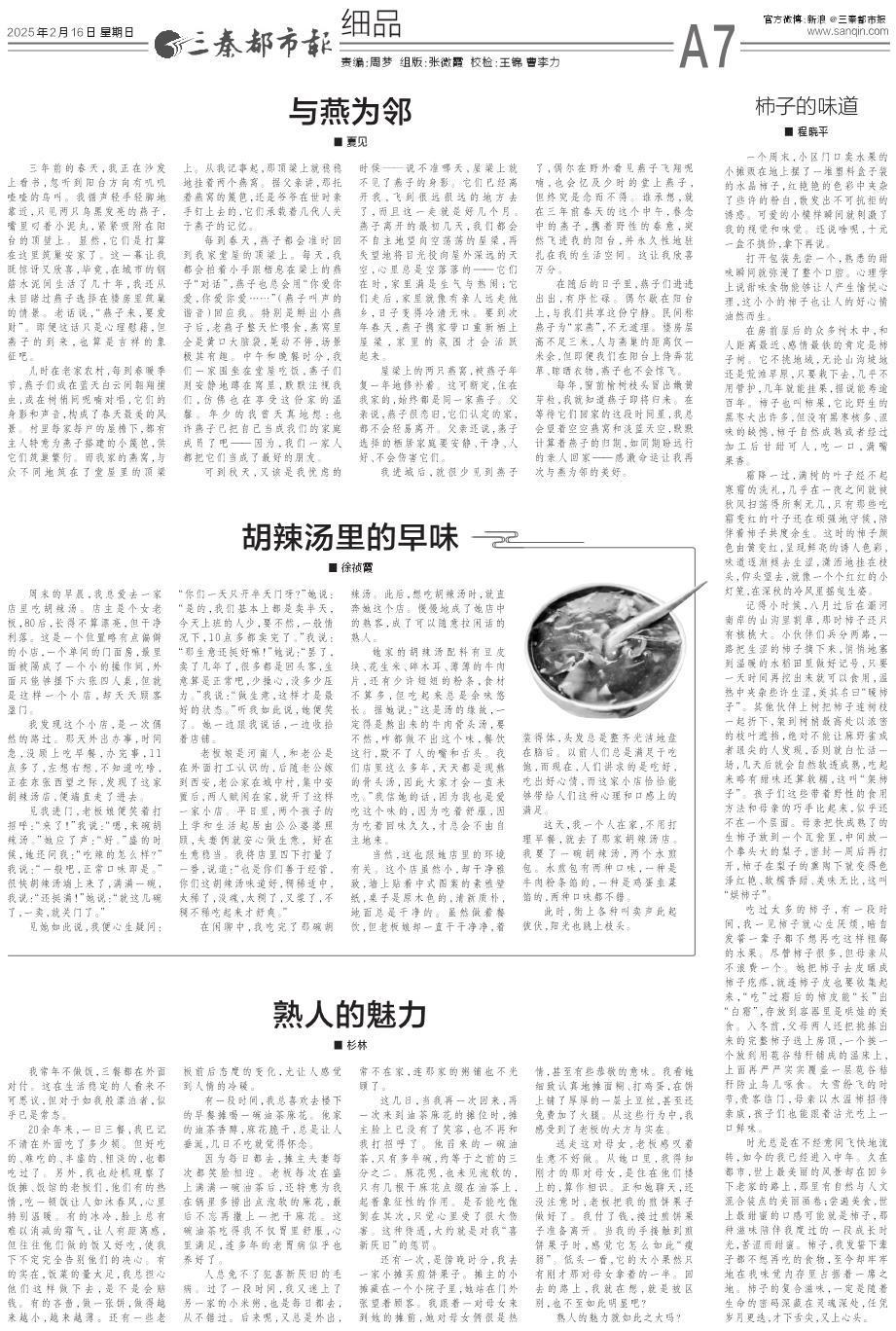
 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964号
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964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