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王惠武
5角钱,对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我来说是不小的面额。
平日里,我能拿到手的最多是5分或者1角的零花钱。只有在过年的时候,才会从父母给的压岁钱里拿到5角钱。对于孩子们来说,盼过年,拿上这一张张5角钱是最开心的时刻。
一过腊八,我和哥哥姐姐便开始掰着指头盼过年,那种期盼的心情直到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结束。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母亲一起赶集,小镇的集市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,走30分钟左右就能到。要过年了,往常不大热闹的街道被人来人往的行人拥堵得严严实实,采购年货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喜庆。
母亲要盯的是谁家摊上的猪肉又便宜又肥厚,根本不去看什么肋排,况且那个时候,也没有把肉的品类分得那么细致,当然不是谁想吃肉就能吃得上,要凭票才有购买资格。搞价是集市上最常见的行为。买卖牲口的,粗糙的手都很神秘地在棉袄袖子里不停地伸长倒短。在等待中,母亲终于完成了选购和搞价环节,带领我们赶往卖小吃的地方。
年夜饭是我们的重头戏。平日里不舍得吃的白面馍、糖包子,都会被手脚利落的母亲提前给我们准备好。在父亲的带领下,我们贴对联、包饺子、拉风箱烧火,过油、炸麻花、麻叶……当萝卜拌肉的饺子端上桌子,热气弥漫在我们的眼前,此时我们应该是最幸福的人。
看春节联欢晚会是过年的一个重头戏,小区旁边的水处理站是大家共同奔往的据点。天还大亮着,我们便会早早搬上几摞砖头,组成凳子,眼巴巴地守着,就怕被别人占据了好的观影位置。刮风还不怕,怕的是刮风又下雪,大人们熬不住,很快离开。而我们小孩子,不到电视屏幕里闪现出“再见”,是坚决不离开的。
大年初一,一早便穿上母亲给准备好的新衣服,给长辈磕头拜年,牢牢捏紧父母给的5角压岁钱,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。这个时候,商店门口小商贩摆放的花炮就是我们这些男孩子最抢手的商品。家里我最小,父母每次也给我的最少,只能把买回来的鞭炮拆开,一个一个放,怕早早放完了,被其他孩子笑话。女孩子们此时就会相聚一堆,炫耀自己的新鞋和新衣服。
小区不大,但邻里关系非常好。大年初一,父母便会领着我们走东家串西家地去拜年。一把瓜子、几颗糖,相互的祝福和对来年美好的期盼,汇成了最美好的音符,成为难忘的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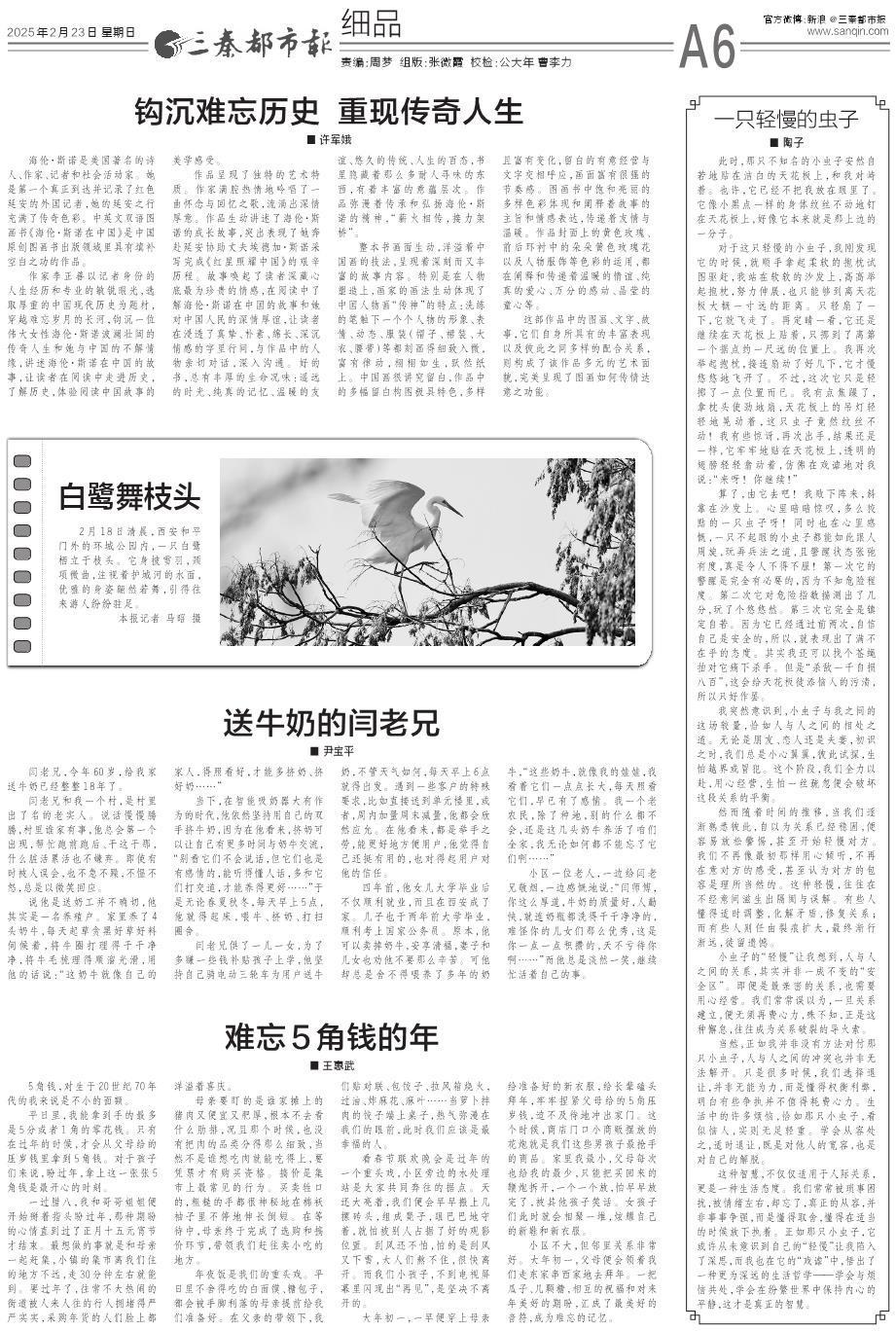
 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964号
陕公网安备 61010302000964号